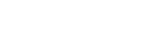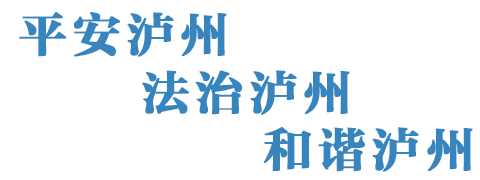□ 许岚枫
很早就听说过《人生》,马云、贾樟柯、王安忆似乎都从中找到了些感觉——《人生》中有人生的烙印,读《人生》启迪人生。
《人生》是路遥的中篇小说,一经刊发即轰动全国。小说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背景,以城郊结合的陕北乡村为故事发生地,截取了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高加林24岁时的人生断面。以从被挤出民办教师到走后门到县城当了记者,而后因为追寻理想爱情被人揭发,又重回农村当农民为主线,引入高加林与刘巧珍、黄亚萍的爱情纠葛,塑造了高明楼、刘立本、高玉德、高德顺、张克南等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,描述了不同地位、阶层,不同际遇、思想的一群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念、生活状态,贴近乡土、贴近现实。曾经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,在广阔天地里挣扎过、奋斗过的人,特别是那些走向未来仍保持赤子心态的人,最能被引发共鸣。
小说把高加林定位于一个很有能力素质的青年,他是高中生,在那时的农村十里八村也找不出几个同等学历,比现在的大学生还金贵。他有悟性,当记者风生水起;有本事,吹拉弹唱样样行;有上进心,一直想跳出“农门”;有人才,潇洒漂亮;有理智和好脾气,从不胡搅蛮缠自暴自弃。这样的人,女孩子怎能不喜欢呢?刘巧珍对他一片痴情,在民风还比较保守的农村,去追他,为他带烟、帮他卖馍、听他劝刷牙,不惜与父亲闹僵,在得知他另有新欢后又祝福他,甚至在与马拴结婚后仍为他向高明楼求情。黄亚萍热情追求他,不惜与前男友张克南分手,把自己的工资随意花在他身上,为考验他叫他冒雨出去找小刀,准备动用父亲的关系调他到江南。最终,高加林还是一败涂地。他嫌弃刘巧珍不识字,没有共同语言,他似乎与黄亚萍志同道合却没有正式编制……
小说里有高明楼的巧言令色、马占胜的投机钻营、张克南妈的自私阴险,都着墨不多,点到即止。如高明楼对改革形势的担忧和妥协,马占胜受处分后的自我反省,张克南妈与张克南在揭发高加林走后门被清退后的争辩。小说里始终贯穿着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憧憬,隐晦地表明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。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显得不近合理甚至冷血,如高玉智的铁面无私,高加林记者才气的埋没,但在更高层次上,展示着全社会向着更加文明友善的方向前行。小说中对此的回应是“今天的政策也对头了,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”,尽管,这是以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失落为代价。时代的光芒影射到个人身上,竟是难以承受之痛。此情此境,人生何往?路遥自有办法,即隐匿于全书的中华文化。
优秀的中华文化,有时并不是以识文断字为基础。它自有一套中国式逻辑,散发着历经苦难仍旧韧性强劲的生命动力。书中的老光棍高德顺就是其代言人。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却极有威信,润滑着高明楼、高加林的关系,对人生经历种种认识清醒,对后生晚辈极尽良善引导,诸如“这么大的小子,还不懂人情世故!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啊”“娶个不称心的老婆,就像喝凉水一样,寡淡无味”“一个男子汉,不怕跌跤,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”。这是对生活的描述也是对人生的反思,是向阳而生、追光前行的精神和文化注脚。
路遥没有以悲剧收场《人生》结局。路遥对人生一世的阶层跨越、青年入世的磨难成长,有清醒而透彻的理解。这是他的极限,也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时代反射。看过小说,读者对高加林的记者能力有目共睹,他应该算是优秀的记者,但因不是正式编制而失去了记者身份。当然,这不是宿命,也不是认命,而是换个方向再出发的一声号角。在不幸面前,个人也是可以选择的,与其撞倒南墙不如就此翻开新的一页——或许正是为了强调这点,路遥让刘巧珍在遭遇背叛后选择了和解,让张克南在恋人被夺后选择了理解,让高加林得到了村民的包容。这对于当今社会上个别人被一时的困难和厄运打倒而选择走极端者,不啻当头棒喝。
相信和构建起一个和谐、包容、向善的社会,让人意识到青年成长往往需要经受社会锤炼,在跌倒后首先归因于自己,而后站起来,调整心情继续出发。这或许就是《人生》入选“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”,至今仍为很多读者推崇传播的原因吧?毕竟,大多数人都相信:向善向上改变命运。
掩卷而思,想起最后章节下注的“并非结局”,想来路遥原本还想给《人生》做后续的,只可惜天不假年……
读《人生》,品味更好人生。
(作者单位:四川省监狱管理局)